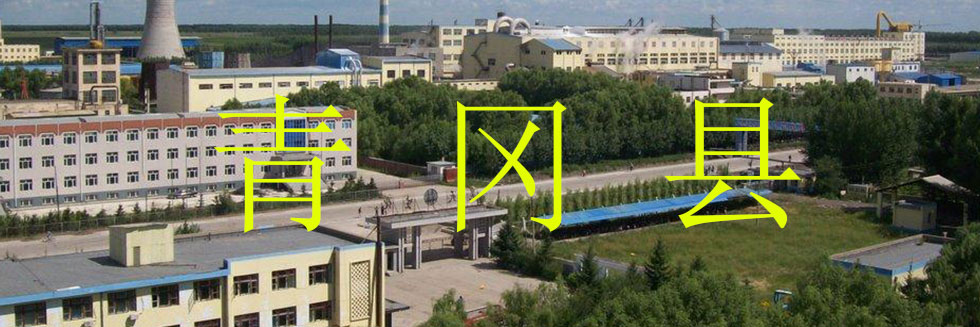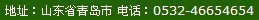|
白癜风皮肤健康 http://m.39.net/pf/a_4478254.html 州县德政 元丰八年(公元年)二月宋哲宗赵煦即帝位,次年改元元祐。谢良佐进士及第后被放外任,从哲宗嗣位元丰八年到元符三年,前后共计十八年时间。前十年,谢良佐先为县学正,后擢升为州学正再至县丞,主管州县教育教化。主要负责当地州县学即学宫的设立和完善,学舍的修建,学田的置办,文庙的管理祭祀等。而在学正任上,可谓是举步维艰,虽经历了诸多坎坷磨难,也都流芳州县。 北宋初年的洛阳地区,是唐末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重灾区,是兵祸迭加之地。在“安史之乱”中洛阳两次失陷。先有安禄山称帝,后有史思明之祸,中间又有回纥人的烧杀抢掠,使洛阳地区的人口骤减三分之二,当时洛阳已成废都。到了宋初,民间十室九空。在封建社会,农业人口是发展经济的第一生产力。人口稀少,就意味着财政困难。到了谢良佐为学正时,虽经恢复,但宋朝的常年对外用兵,捉襟见肘的州县财政也很难拿出多少银两用于教育。 谢良佐立志德化乡里,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激励着他经常游走于州县之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在地方长官和州县士绅的支持下,从一州一县做起,取得经验,推而广之,历经十数年之努力,终将州县官学、文庙焕然一新。使士子得以教化,民风得以淳正。正是在学正任上孜孜矻矻地努力,绍圣二年迎来一通诏书,升任渑池县令。 渑池地处豫、陕、晋三省交界处,属浅山丘陵地带。古有崤函关隘和秦赵会盟地,为兵家之必争。历史上战乱频仍,匪患迭出,民间疾苦自不待言。 谢良佐初任渑池,则是满目凄凉景象。任职四年,从整顿吏制,劝课农桑做起,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涵养民力,渑池逐渐变得风清气正,士民乐业。另一方面,推进县学、书院、文庙管理,修葺云门古寺,使民间信仰有所托寄。公干之余在书院、学宫为士子讲学。积数年之功,渑池大治。离任之时,县人十里相送。 哲宗元符元年(公元年),谢良佐转任湖北德安府应城县令。 应城县古称蒲骚,县东南部大片沼泽,与云梦泽相连;西北部为丘陵高岗,为古郧国边塞之地。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农耕文化欠发达,民间生活相对寒苦。 谢良佐治应城,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又立信治讼,劝课农桑,兼以德化以教。 整顿吏治以勤政为主。从县府官员到衙役,各司其职,不敢懈怠。胡安国初见谢良佐,见庭中吏卒,如土木偶状威武直立,使人肃然起敬。调解民事纠纷,以立信为主,力求简而无讼。 《上蔡谢先生语录》中,通过与学生曾恬对话,记述了谢良佐治吏和判讼的一个侧面,展示了大道至简的治政方略。 问:“如何处理政事?”谢先生说:“我做县令,首先立诚信给大家看。开始事务繁杂,我的诚信规矩建立之后,现在事情就简单有序了。凡事都与大家商议,选择一个最佳方案。比如借贷,就先约定利息不能超过本金。既然息不过本,就按实际的月数、天数偿还。又规定还款期限。超期不还就治罪。如果利息超过了本金就不再受理。凡是县衙中受我节制的小吏,我向他们说明所办公事的要求是什么,而且不再改变。在规定的时间内事情没有了结,就治他们的罪,绝不宽贷。所有这些都是表示我树立诚信的规矩。”又问:“处理事情怎样得其要领?”谢先生说:“拿一件事举例。比如让捕快把案人带到,便让人将原告、被告、证人带上开说:谁是原告,谁是被告,谁是见证人,很快就可以清楚案件原委。” “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淳化民风,从富民和教化入手。 在发展经济上,应城西北部以水旱间作农业为主,鼓励垦荒和山坡植树种竹,东南部泽湖区除水田耕作外,鼓励发展蒲草编织,莲藕种植和渔业,加固堤防,确保河湖安澜。通过轻摇薄赋,涵养民间财力。 待经济稳定发展后,整修县治,修葺仓廪。兴办教育,延纳名师。先后兴办书院、学宫和孔庙,收公田归学宫,保证教化有依,教化设施焕然一新。今日之应城市,学宫(孔庙)尤在,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谢良佐公余授徒,“言论闳肆,善于启发,”一时学风大兴,学者蜂至。在北宋末年,应城上蔡书院,声名鹊起,从这里走出去一大批名人大儒:如晋江人曾恬,官至南宋大中正;胡安国,建宁崇安人,官至南宋中书舍人兼侍讲,并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宏,胡安国次子、南宋承务郎、理学大师,湖湘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和主持者;胡宪,胡安国从子,官至南宋迪功郎,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其得意门生;郑毂,建州建安人,重和元年进士,御史台主簿,秘书郎;朱震,荆门人,北宋南宋著名大臣,理学家,汉上书院创办者,荆门三贤之一;还有陈叔易,康渊等一大批重臣名人。胡安国父子在湘潭建碧泉书院,不仅为当时培养了大批名流重臣,也为之后的湖湘文化经久不衰积累了丰厚的基础。又有晚期门生詹勉、谢袭、朱巽、毛有诚、符生等人。符姓门生,录有谢良佐语录九十七条,早佚,为后世不传,实属遗憾。 元朝应城令谢祖锦在《谢公祠记》中曾感慨道: “上蔡谢先生昔治蒲骚(应城),其化民以德,期于无讼,简而能栗,威而不猛。是能保我黎民亦有辞于永世!去之日,父老思之深,慕之笃,立祠祀之示不忘也。文公朱夫子记云:胡文定公以典学使者行过邑,执弟子礼。其道隆德尊何如,非同时相知者乎。是邑乃先生过化之所,今民淳俗美,先生遗泽存焉”。 谢良佐任应城令上,可谓是将内圣外王之道发挥到了极致。 谢良佐元符三年末(公元年)调入京师后,当地人感恩戴德,在应城建谢公祠以示怀念。应城谢良佐祠堂是湖北、河南、浙江几处谢先生祠中设立最早的。自宋元明清屡毁屡新,可见谢良佐在当地影响之深远。应城上蔡书院与谢公祠为同时期,也是在全国几处上蔡书院中设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在湖北应城,人们视上蔡书院、谢公祠为神圣,充满敬仰之情,是圣殿级的崇拜。 京师不遇 北宋元符三年岁末,谢良佐应城令上奉调回京。由于其屡仕州县政绩斐然,朝野上下有口皆碑,遂被吏部力荐回朝做官。事有不巧,对谢良佐德化文章颇为欣赏的宋哲宗已于当年二月病逝。因哲宗无子,朝廷立哲宗之弟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为帝。 赵佶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传说赵佶为南唐后主李煜托生,虽不足信,但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赵佶自幼酷爱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有非凡的天赋。年长后又迷恋青城,寻花问柳,京城有名妓女无不与他有染。在位二十七年,自政和以后的十七年很少坐朝听政。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载: “上自政和以来为微行,每出乘肩舆,并无呵卫,前后数内臣导从,而民间指目为‘小轿子’。置行幸局,主供帐、饮膳等。局中遇出,即称‘有排当’。次日不归,即传旨称‘疮瘍不坐朝’。閤门等处日有探侯,闻有排当,即知必出;闻不坐朝即知不归,卒以为常。始犹外人未尽知,因蔡京草表云:‘轻车小辇,七次临幸’,邸报传,四方尽知之矣。” 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却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尝鲜,寻求别样刺激,尤爱“飞将军”李师师。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侍从数人,到李师师家过夜。专设行幸局服务其外出寻欢作乐,当日不上朝就说圣上有排当(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圣上有疮痍(染病)。对于这位“青楼天子”之秽行,大多数朝臣都心知肚明而不去说破,而耿直之臣曹辅则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阅罢勃然大怒,立命宰相王酺等人,以诬蔑天子罪发配郴州。 在用人上又专宠蔡京、童贯、王酺、高俅等奸邪之人。当有人对徽宗宠幸善蹴鞠的高俅提出质疑时,徽宗居然说“你们有他哪样的脚吗”?其歪理邪说让人无语。 似这般昏聩之君,大好河山交与其手,北宋不亡都难。 靖康之变,徽宗在被虏北行途中,蓦然见杏花开,悲从中来,赋《宴山亭》: 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其相思极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读,被王国维称作“血书”。个中凄哀悲凉与南唐后主李煜又何其相似。当初立赵佶为帝时,有人谏道:“端王轻佻,不能君天下。”后人评价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了解过徽宗作为,就难怪谢良佐元符末回京多时则被冷落一旁了。后在吏部再三提醒下,徽宗召见了谢良佐。一个是豁达耿介,一身正气;一个是声色犬马,又刚志得意满,君臣相见,在廷对中自然是言不投机。一番别扭的交流后,谢良佐认为“上意不诚”,就退而求其次,任书局朝奉郞,官阶五品。朝奉郞就是个闲散官,谢良佐不习惯这种无所事事的散官生活,不久,便自求西京(洛阳)竹木场任管库。次年(公元年)春,徽宗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前朝唐德宗李适(kuò)建中年间曾发生“泾原兵变”,德宗出逃。谢良佐与人闲聊说建中年号不祥,“恐亦不免一播迁。”遭人举报后,徽宗大怒,谢良佐获罪下狱,虽经多方营救不久出狱,终被废为民。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受尽百般屈辱,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处),还是被谢良佐不幸而言中,这是后话。 《圣经》上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以飞语坐罪而终结仕途,这是谢良佐人生道路上的大挫折,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常人当是莫大的打击,而对于圣贤遭一大厄,必增一份光芒。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作为精通经史早已看破世俗的谢良佐,只是人生的否泰转换,心理上很快释然,这就是贤者与凡俗的最大区别。卸下案牍劳形和朝乾夕惕的仕途纷扰,反觉一身轻松。身心稍事调整,便在县城南关故宅开馆授徒,全身心投入到著书立说和英才教育。这就是上蔡县上蔡书院的最初雏形。 明嘉靖初总兵,官督漕运、《漕运通志》的作者杨宏《上蔡先生语录后》:“以先生之道,假命得志于时,身秉国钧,必能有所建树,卓卓表现于世......后卒以谗去归,意者德盛则招尤,学成则生忌欤?虽然,祸患之作,庸俗人处之,则抑郁不能自解。至杰出之士,则淡乎相遭,漠乎相遇,岂毫末增损于其间哉!” 康熙亲赐“天下第一清官”、清朝雍正年间礼部尚书、“礼乐名臣”张伯行,晚年曾评价谢良佐:“沉顿下僚,历落坎坷,则上蔡先生为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学,诚得一展所长,其英爽磊落之气,足以修政立事……其所鐘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学而得其统宗。乃遭际坎陷,不获发舒与朝者,则天也。上蔡何憾焉!” 谢良佐晚年,心无旁骛地整理文稿和专注授徒,为人生的最后一站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走完了人生中最惬意淡定的一程。(来源:上蔡发布) (未完待续)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qinggangzx.com/qgxtc/12540.html |
当前位置: 青冈县 >上蔡文苑蔡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周靖一代宗师谢
时间:2023/4/2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任仲平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纪念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