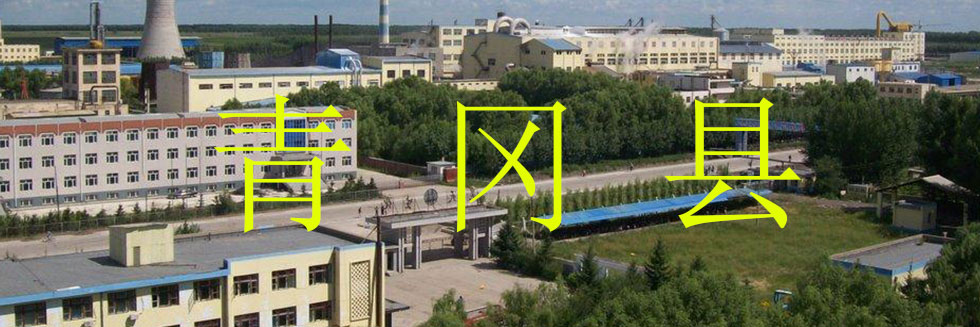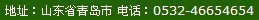|
作者简介:薛春梅,女,四川平武人。在公开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乾陂沟人舞“狮” 文∕薛春梅 乾陂沟老话爱说“娃儿望过年,大人盼找钱”。可我这个中年人也盼过年,说起过年,耳畔总有“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回荡。这是老家乾陂沟耍“狮子”的锣鼓声。乾陂沟人不说舞“狮”,说耍“狮子”。一个“耍”字,看似轻轻巧巧,实则要多年的功力练就。 说到乾陂沟的“狮子”,就必须说说宏才爸这个领头人。他是我们薛家的长辈,是一个精通一些奇门暗技的人才。除了不喜欢种庄稼,耍狮子,理发,打鱼,算卦,做美食,……他会的还真多。在当时的农村,肯定很多人是嫌弃他不务正业,放到现在就是多才多艺。薛家在乾陂沟是大姓,据说还是“薛土司”的后代,我们不像北方那样叫叔伯,跟自己父母一辈的,男的就在名字后面加一个爸字,女的就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孃字,喊起来一长串,却透着亲热,有一家人的味道。 过年耍狮子这个传统保留节目,我不知道在薛家传了多少辈人,也不知道以前是否也是这么威震八方,年年在小县城稳坐第一把交椅,甚至最远耍到了中坝城。反正在我小时候,快过年的时节,就忙的很,应该说我们一个院子十多个娃儿都忙的很,着急忙慌干完大人交代的事情,放起小跑去宏才爸家。宏才爸家闹热着呢,进进出出的都是人,剪纸的,描红的,划篾条的……有条不紊地准备扎新狮灯。有时候大人喊回家吃饭都不情愿,生怕错过了哪一个细节,又吃了多大亏似的。要不飞奔回去装一碗饭,挟点菜在上面又跟到跑回来。“眼睛看憨了”老年人这样训不晓得吃饭光晓得憨痴痴看人家的娃儿。 宏才爸在我家隔壁,一层木板之隔。按说我占据有利位置,可家务事多啊,听着“咚咚锵”,心头猫儿抓样,还得强忍住,得空就去瞅一眼,生怕母亲晓得了,“笋子炒肉”滋味长呢。 宏才爸他们从冬月间农闲时候开始准备,要到腊月二十几才能正式开演。每一道工序都不能少,一笔一划都要勾到位,该粘贴几层纸,一点也不能马虎。当我在城里遇见的那些耍“狮子”的,浮皮潦草的狮子头,一节花布狮身,用不了几天就能草就的狮子,我心里有难过也有愤怒。随便在店铺门前晃两下,就说给钱给钱。难过的是,这跟我小时候看过的狮子,千差万别啊,怒的是你演不好也罢,画个像样的狮子头啊。总觉得他们亵渎了狮子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形象。 等到狮子头完全被红红绿绿的新纸层层覆盖,头顶的九个包,宏才爸要亲自糊的圆润妥贴,然后叫润才爸或者清哥拿毛笔描四周环绕的云彩,他们俩是毛笔字高手。还要在狮子的舌头上写上“吞瘟”两个大字,表示狮子能除瘟扫害。狮身是一床被面大小的麻布做成,表演的时候不容易看到人的腿,更逼真,更有威慑力。两个铜铃大眼,怒目圆睁,阔嘴红舌,金黄色的发须,一个威风凛凛的狮王诞生了。 耍狮子最重要的角色是狮子,头尾各一人。特别是耍前面狮子头的那个人,随时要举几十斤重的狮头,身要高,腰要有劲,开始是宏才爸,后来宏才爸背微驼,就由高大的喜才爸担任了。人高举狮头的时候安逸,多数时间是匍匐着身子,累人呢。耍狮尾一般是水才爸和伟才爸,他们两个子小些,其实耍狮尾巴的人也恼火,你要倒退着走,用手去摆动尾巴,遇到调皮的小孩子会去踢尾巴。好在伟才爸是“上甘岭战役”回来的,练过一些功夫。 狮子前面是“笑和尚”,专门逗狮子的。诺大一个竹编纸糊制的头盔,画上白色油彩,眉心点一枚红朱砂,一对大而夸张的笑眼,格外小巧的鼻子,裂开憨笑的大嘴巴,憨态可掬可爱至极。后背用红布做的长头发。手里拿一马尾巴做的“文刷子”,伴随锣鼓声,时而作状给狮子吆蚊子,时而跳跃,时而扑腾,时而坐地,时而登高,逗使狮子抖舔毛皮,摇头摆尾,卧地点头,跳高桌等高难度动作。 首演就在我们竹园的院坝里。天擦黑边上,屋檐上点起一串红灯笼,特地把那一对六棱柱的跑马灯郑重其事地挂上,照得街檐红彤彤的,给每个人的脸上打上一层红晕,有了厚重的舞台效果,黑黢黢的大山就是天然的幕布。“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声越来越密集,田坝里的,店子上的,青冈边的,包括石坝里的,一河坝的人都打起灯笼火把往竹园里赶,跑的最快的自然是孩子们,锣鼓就是命令,就是召唤。我们竹园里的娃儿因地利,早就等的不耐烦了。宏才爸还在连比带画地教打钹的,该听哪个节点,记不住你就把“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记成“等狗去,等狗来,等到狗儿来了才开台”。我们也跟到唱:“等狗去等狗来……”后来才明白是要等人到的差不多了才开始。 “今年狮子耍的好哦”宏才爸朗声唱道。 “哦——”众人应和。 “狮子头上九个包哦——” “哦——” 喜才爸高举狮头。铃铛作响,狮眼滚动,神气活现,狮子威风凛凛,百兽之王风采尽现。笑和尚的“文刷子”往左,就左边打滚,往右,就右边打滚,笑和尚在前面给观众作揖,狮子在后面卧住不理不睬,见状作势要去打狮子,狮子忽地起身,咬住笑和尚不放,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表演结束后,就从我家开始巡演。巡演,主人家接待,要在堂屋里“摆礼行”.这个礼行可以是适当的现金,也可以是烟,看主人家各人的心意。有讲究的人家还可以“摆阵”,阵分文阵和武阵。文阵一般是对对联和写毛笔字,武阵则是狮子爬高,几张八仙桌往高里重叠,爬的越高礼行钱就越多。据说还有爬又滑又高的卷成筒状的簟席,想想都觉得厉害。 记忆最深的是我和冬梅两个摆了一个文阵,在乡下摆武阵的居多,大家都觉得好奇,我们觉得好玩,两人分头回家拿鸡蛋换了六包烟作礼行。嘀咕一阵,想出一句:田坝麦生叶叶绿。觉得好对嘛,我们这里的薛家的三个大院子:田多的叫田坝里,靠近青冈林的叫青冈边,竹子多的叫竹园里。下句就对:竹园竹长节节高。我们就满意了。谁知锣鼓一敲,狮子舞起,宏才爸朗声吆喝道:“竹园二梅生的好哦” “好哦——” “出题出的妙哦” “妙哦——” 后来对没对出来不记得了,只记得开心的不得了。一个生来腼腆内向胆小的人,居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这本身就是一件勇敢而开心的大事,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往往在这家刚刚看过,我们一群小孩还要撵下一家,其实很多招式大同小异,可就是觉得开心,笑过好多遍依然觉得好笑,十里八弯地跟;天黑路窄,一脚高一脚低地摸索着跟;有时候梭到土埂下,爬起来继续跟,簇拥着狮队,好像自己也了不起,有点小得意,常常晚饭顾不上吃,回家翻碗柜找冷饭吃。 往事悠悠,多年过去,年轻高大的已经佝偻着背,行动迟缓,特别是宏才爸,已经作古。我还记得一头卷发的他,随时笑眯眯的,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幼儿园动物园的儿童时代,领了很多杂耍班子来院子里,小狗骑车,猴子做算术,骆驼表演,有啥新鲜点的都要带回来,不用给钱,他好吃好喝招待别人。 现在,再也看不到像乾陂沟人那样认真而精彩地舞狮了。怒目圆睁活灵活现的狮子头,那夸张而快乐的“笑和尚”,“咚锵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只有在梦里,在过年闪现回放。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鍖椾含鐧界櫆椋庝富娌诲尰闄?娌荤枟鐧界櫆椋庡尰闄㈠摢瀹跺ソ
|
当前位置: 青冈县 >民俗征文选登薛春梅四川平武乾陂
时间:2017-9-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好玩初行西藏这9件事是必做的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