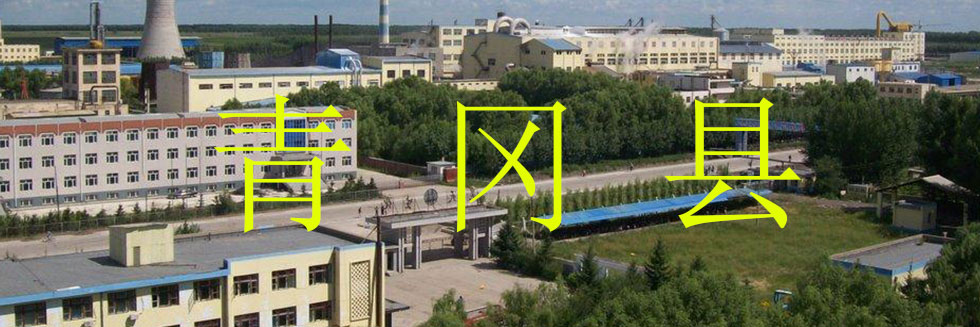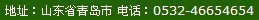|
多平台免费发表作品!你比任何大师、名家都重要! 点击动图,进入投稿页面! 郑春龙,年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防大学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北京通州油画学会理事,解放军美术创作院创作员,解放军摄影学会理事,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作品入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第二、三届中国油画展,人与自然第二届当代中国油画风景展,纪念建党80、90周年全国美展,庆祝建国50、60周年全军美展等。《节日》荣获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美术类金奖。《黄土地的记忆》获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佛境》获第五届中国西部大地情全国画展优秀作品奖。先后在郑州、淄博、本溪、潍坊、昆明、长春、北京举办画展。出版《实践与创作·游记·油画》《郑春龙油画》,作品被美术馆、有关机构和个人收藏。 联系 王伏焱 上帝解散了工程队 圣经中记载,人类为了展示力量,啸聚在示拿这个地方,要修一座通天塔。三人成虎,这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事件。耶和华使个阴招,通过变乱人们的口音和语言,彻底铲除了他们彼此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于是,大家只能干嘎巴嘴,大眼瞪小眼,相当于脸对脸就失联了,建塔工程队只好解散,遗下半截子通天塔,千秋万代地杵在那儿,成了烂尾楼。 问题来了—— 问题1,上帝为什么不容许人类修建巴别塔? 问题2,人类究竟为什么费劲巴力非要修建巴别塔? 看圣经的意思,人们修这塔是为了展现“团结起来力量大”,跟上帝叫板的意思。这样的活动显然忤逆犯上,上帝当然要全力打压。 我没有系统研读过《圣经》,没有判断这桩公案的硬实力,因为看了一个人的画,思想的枝杈七岔八岔不知怎么就联上了这一段,就想到巴别塔怎么就成了烂尾楼—— 艺术的态度和文化的立场 对于郑春龙其人其画,我熟又不熟,或者不熟又熟。我们很早认识,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时候,那年我刚从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把自己倒腾出来,落脚在大庆坦克旅,刚好我和他同在政治部宣传科共事,当时他刚刚考完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的文化课。约一个月后,我调到集团军政治部。一到哈尔滨,他就张罗请我吃饭。那天,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做了一桌子菜,铺天盖地的,和后来看他的“秋葵系列”油画感觉上差不多,时至今日,那两口子做的那条比桌子半径还要多出几个厘米的红烧鲤鱼,喷出的香气,仍然觉得呼呼打脸。没几天,他到北京上学,蹽杆子了,再见面,已是二十多年以后,他已然宝马金鞍牛逼闪闪,是中国地面上可以掰着指头数得着的画家了。 去年夏天,我顶着燕赵天空毒辣的日头去国防大学美术馆看他的画展。我们重新见面了。我见到了他的画,一边看,一边就想到八杆子打不着的那座“烂尾楼”。 时至今日,我与郑春龙没有聊过一句他的油画。在这里,我不强调他是个画家,是不想把“行业标准”作为评判他的艺术的标准。他的画是具象写实还是抽象表现,造型准确与否,色彩语言是否丰富,在我这里都不再重要。我看重的是,他的艺术,或者他的画,是不是提供了一种与我的当下生存有关的新感觉。换句话说,郑春龙的艺术,是否让我能够真实面对我自己当下的生存体验和感觉。 套用一句现成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此,所有的艺术都应该具有当代性。因为,人类生活的图景不管多么美妙玄奥,也必须永远绘制在当下的“画布”上。艺术当代性的体现,源于艺术家必须具有一种“真诚表现力”。就是说,能够提供一种与当代人生存体验有关的思想或情感的艺术作品,才是真诚的艺术。这既是艺术的态度,也是文化的立场。 群山重重 不知什么时候起,反传统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艺术发展指向的风向标,甚至,竟然有幸让一些政治人物借用,拿去变通为某种政治隐喻和口号:不破不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延至“改革开放”,及至中国美术“八五新潮”,中国艺术几乎武断地认定,艺术史就是不断打破传统不破不立的革命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艺术“政变史”——印象主义顶了古典主义的肺,野兽派端了印象派的锅,表现主义横扫天下玉宇澄清万里埃,传统艺术差不多让杜尚用一把尿壶(作品《泉》)就给颠覆了。看吧,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里,已然用三个大咖的英雄事迹给了我们这样的示意:塞尚觉察到印象主义专心于飞逝的瞬间,勇毅而果断地抛弃了印象主义“凌乱不整的光辉夺目”,坚持了自然的坚实与持久的形状,最终导向了起源于法国的立体主义;高更完全不满意他所看到的那种生活和艺术,渴望某种更单纯更直率的东西,干脆一头攘到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指望能在原始部落中有所发现。他那些诞生于土著姑娘们肚皮上的野蛮画作,任由后人意淫领会,直接导向了各种形态的原始主义;而梵高呢?那个用剃刀割了自己耳朵的疯子,这事儿上比那俩哥们儿悟得更透,蹽得更远,一眼看死了印象主义——印象派由于屈服于他们的视觉印象,由于除了光线和色彩的光学性质以外别无所求,那么,艺术就处于丧失强烈性和激情的危险之中了,只有依靠那种强烈性和激情,艺术家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结果,梵高的冷血和疯狂却把冷静和理性的德国人忽悠了,向来不苟言笑的日尔曼艺术一头扎进了表现主义的汪洋大海。 在中国艺术家或短或长或不短不长的有限的艺术生涯里,那种以汉字符号形式作为承载方式的艺术历史和艺术史观,那些叽叽饿兽般扑到他们眼前的文字,无不一本正经且言之凿凿地言训谕着他们:艺术的出路在于打破传统的束缚。所以,塞尚之所以成为塞尚,高更之所以成为高更,梵高之所以成为梵高,是因为他们后脑勺子都长着反骨——他们不尿“传统”这一壶!想成为大师吗?看到没,得这么玩! 但是,是这样吗? 库尔贝的风景画中,海边的石崖显现了厚重而斑驳的色层,给了莫奈很大的影响。同时,库尔贝用画刀作画的方法丰富了油画的技法,成为了很多画家的喜爱,塞尚在早期肖像作品中用画刀来塑造形体。斯塔埃尔以画刀作画,成为对自然景物抽象的一种表现方法。梵高疯狂迷恋过日本的木版画,他的艺术也曾盘旋在印象派的光影之中。塞尚本来就是印象派队伍中的一员实力画将。而股票经济人出身的高更,是参加了几次印象派的沙龙展出之后受到蛊惑,拒不听从一个叫毕沙罗的哥们儿的劝说,铁心铁肺地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马蒂斯本能地赞美罗浮宫收藏的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以后又赞美东方艺术。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上,他首次接触到东方美术作品,波斯细密画向他展开了他的感受的全部的可能性。老马认为“这种美术以它的性质暗示出一种更巨大更真实的造型空间”。甚至,他认定,“我的启示来自东方”。晚些时候,莫斯科城那些圣像又打动了他,于是,他开始了解拜占庭绘画。这些经历让他见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当你看到自己的努力被这样一种古老的传统肯定时,你最好是任听它的摆布,它会帮助你跳过壕沟。” 大卫·霍克尼的牛逼,无疑是国际级别。都知道弗洛伊德更是出名的牛逼,英女王伊丽莎白请他为自己画像,请了73次才请得动,女王成功地得到一张A4纸大的画像。弗洛伊德给大卫·霍克尼画的肖像画,跟伊丽莎白的尺寸一样大。在创作《科罗拉多大峡谷》时,大卫·霍克尼遇到了麻烦。他遇到的麻烦也是西方绘画的麻烦。西方绘画是将色彩铺在画面上,用明暗、颜色、光线来展现对自然的审视。而中国画以特定模式进行视觉表达,让人感知。中国人用的是“三远法”的散点透视,不是固定一个视点,是在观游中不断变化视点,画的是综合景象,是对山水烟云的感受,是“画可以补江山之不足”,营造出对自然的审美,表现更高的精神需求。大卫·霍克尼正是受到中国山水画、特别是长卷的影响,才摆脱了他面临的“西方困境”。完活儿后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经过拼合,呈现出多视角、多方面的立体画面,让这个英国老头儿不得不服——中国人发明的“观游”最神奇的地方,这种时常切换观看角度的观察视角,对人类艺术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当如何对待传统?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大学某教授在评论画家戴士和时写道:“油画到了戴士和这里,就像佛教到了慧能那里一样,原来的规矩和法则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是明心见性和自由表达。”此处不想讨论戴先生的绘画,也不想与该教授这种生拉硬拽的比较作论争,只是就六祖慧能的“顿悟禅”说道一二。世人皆知六祖文盲,是个目不识丁的山野樵夫,标准的无产阶级,但其绝非不学无术、潦草佛法之徒,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亦非“原来的规矩和法则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之结果。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任何顿悟必须有明确的思考问题作为大前提,同时顿悟必须对此问题经过长期、认真、甚至艰苦的思考才可能出现。我相信,那位教授所描画的那种“明心见性和自由表达”的油画,决不是“破除”礼法成见的结果那么简单随性。如果说也有例外,我们可以帮助吴承恩指认,孙悟空就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可是,一个傻逼都明白,那是猴子的故事。 没有传统的滋养,当代艺术永远是个孤儿。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信念: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当理解本人就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双在传统的河流中被打湿的鞋子。在这个问题上,诗人木心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越得过 有人对我说 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 我说操他妈 经典主义坚忍而剽悍的过往 经典主义的艺术实践,是通过知觉经验创造直觉象征。这种直觉是对生活的一种认识,它具有某种宗教态度的性质,那么,艺术品就是它所表现情感的一个样本。它是基于过去和未来、空间和时间的相互作用之上的,通过它在我们和其他生命之间建立的同感交流,通过它造成我们意识的扩展,把我们引进生命本身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相互渗透和永无止境地持续的创造。形象不能代替绵延的直觉,但是,采集来自不同类别事物的不同形象,能把意识引向精确的点,在那儿,存在着能被把握的某种直觉。这种知觉经验创造的直觉象征,自然顺畅而又磕磕绊绊地将古典艺术由过去导引到现在,期间人们认为,从早期直到当代的画家们艺术进展的连续性中间,存在着断裂现象,而马蒂斯说根本没这回事,他坚定地认为,放弃传统,艺术家只能获得一种转瞬即逝的成功,而他的名字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经典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可疑的,或许就是一种虚枉的存在。于我个人而言,这种类似于“艺术八卦”而“八卦”出来的这么生猛一个词儿,实在是为了便于我针对郑春龙的艺术所频闪的某种“内质”的对应。 郑春龙的艺术带有坚实的经典倾向。 经典的真正意义在于,是我们希望的在传统的全部知识中,维护我们合理的独立感受。读郑春龙的油画,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发现,会慢慢地发现艺术的奥秘,它是由思索自然,思索如何表现永远被现实激起的梦境构成。他是以一种更加介入更为规律的方式,学习和摸索着把每种研究推向某个确定的方向。我们会一点一点看到,“绘画是一种表现手段”开始行使它自身的权力,倔头倔脑地向前挺进。德拉克罗瓦喜欢说“精确并非真实”。于是,在这种艺术语境之下,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种事实:经典艺术家不断重复画同一作品,而且每次都不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塞尚总会画同一幅《浴女》。虽说这位大师不断重复画同一作品,但我们不是总会以最大的惊奇面对一幅塞尚的新作品吗?这是一个惊人的榜样。郑春龙无疑接受了塞尚道德力量的巨大鼓舞,在怀疑的时刻,在寻找自我之际被自己的发现惊吓的时刻,那位艾克斯的大师就会站在他的眼前,仿佛塞尚在说,“如果我是对的,你也是对的”,因为塞尚从来没有犯过过错误。塞尚的作品存在结构的法则,这一点对郑春龙当然很有益处。在塞尚各种伟大的品质中,就是要使色调成为一件油画作品中的有力因素。正是这种情况,同样赋予了郑春龙的油画一种最崇高的使命。 一切都存在于构思之中,所以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整体有清晰的想像。在一切伟大的时期,美术家头脑中最为重要的考虑就是形的本质,大的体积和它们的关系。古代就这样。郑春龙的油画创作,格外重视整体设计和色调控制,一切都尽心竭力地安排得恰如其分,不论你站在什么距离,永远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每个形象。如果画面秩序井然而又明白清楚,这就意味着地起根儿画家头脑里就有同样的情景,要不然就是他意识到了这种秩序井然和清楚明白的重要性。《节日》、《雾中花》和《苗舞》这组“苗女画”,以至《老家》甚至是《秋葵》系列,形象的肢体纠缠扭结,交叉叠加,但在我们的眼睛里,它们不乱不散不粘不滞,挣扎泼命般要与各自的形象联系起来,努力去完成明确结构的使命,让一切混乱自动消失。这些也证实了,他能在不同的日子里,从自然景象直接获取印象之后,通过组织自己的感受,在同样的心灵框架中继续自己的工作,并且发展这些感受。之于此,我们能够判断一个艺术家的生机和力量,这种力量证明了他具有充分的自制力去使自己服从规则。 最单纯的手段就是那些能够最好地使艺术家表现自我的手段。艺术家必须具有一种谦逊精神,相信自己所画的仅仅是他所看到的东西。我相信郑春龙喜欢夏尔丹表达自己的方式:“我涂颜色直到相象为止。”当然他也喜欢塞尚的说法“我要达到相象”,或罗丹“模仿自然吧”的热血召唤。列奥纳多说过:“能模仿自然才能创造。”艺术家在理智地思索时,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他的画是一种技巧。当他绘画之际,应当感到他是在模仿自然。即使他离开自然时,也应该确信,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自然。 其实,我更愿意相信,郑春龙对这些大师的关于“相象”和“模仿”之说,有自己独到的意会和理解。相象的目标和模仿的作法,都不是对自然的拷贝和抄写。他的绘画能够让我们充分相信,他选择颜色并不依据任何科学理论,而是依据观察、感受和自身经验。那些不断重复画出的每一幅“苗女”,成为了让我们惊奇面对的一幅幅新作品,与此同时,我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仅仅是试图摆上能够表达自我感受的色彩。我们会发现,郑春龙对于自己所描绘对象的塑造,是通过大的色块而实现的,是以色造形。《苗女》系列,人物的肤色、服装、银饰和背景,都有明确的色彩倾向,暖白、黄灰、红灰、棕黑,几个大色块的秩序分布,构筑了画面的色彩结构。这不同于印象派的瞬时记录,也不同于古典主义绘画那种格式化的“酱油调”,而是一种理解自然基础之上的创造,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所意向铺展的美与宏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是模仿自然的,它是通过富于创造性地把生命力灌注于艺术品之中来模仿自然。如此,艺术品就会显得那么丰富,就像我们在大自然中发现的一样。为了达到这种效果,需要伟大的爱,伴随一件艺术品诞生,需要保持一种强烈的热情和深刻分析的爱。而爱,才是一切创造的本源。 绘画中,存在着一种起推动作用的色调比例,它会引导画家去改变人物的形或变化作品的构图。一直以来,郑春龙一直尽力去寻找这种比例,不停地找啊找,黑灯瞎火的,像一头饿瘪肚子的棕熊,在野地里翻找农夫遗落的每一粒粮食,这样不停地工作下去,直到在构图的所有部分中获得它。在所有部分都找到它们的明确关系之际,这样一个时刻就来到了:此时,除非整个重画一遍,否则,他要在自己的画上添加一笔都不可能了。 三千年前的两声鸟叫 很久之前读到一篇文章,写《诗经》的开篇《关雎》。文中说,两千年来,解读《诗经》最权威最正统的是《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不信?接着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皇上的大老婆看见一个小女子模样长得俏,于是就急得睡不着。急什么呢?不是急着遣人把小妖精“做”了,而是急着怎么把她弄进宫里做小老婆,从此东宫西宫左右一心,共同辅佐皇上、治理天下。啊哈,真乃“后妃之德也”! 我靠,这不是扯犊子吗! 我相信,三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渭河边,确有一只鱼鹰闲得蛋疼,叫了一声“关!”赶巧了,近旁的一位雌性同类正对着白光光的大月亮卖荫,就随口应了一声:“关”。是夜,也有一个年轻男子睡不着,他听了那两声,心里可就长了草,更睡不着了。 在艺术的广阔时空里,关于真实性的表达,总是会号令天下,纠集起各路英豪一展武功绝学。古典主义的客观再现,印象主义的瞬时抄写,立体主义的多维视角表达等等,艺术家们都在他们自己的时代点灯熬油披肝沥胆地奋斗着,力求做到极致。对此,我的理解是,并不存在新的真理。艺术家所掌握的,于他而言,是由那些重复的流行的真理构成的,不过,这些真理向他显示了新的意义,而在他抓住了它们的最深的内涵之时,他就把它们化成他自己的真理了。个体之外并无法则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都分享它的见识、它的情感、甚至它的错觉。一切艺术都带有其时代的烙印,而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那个烙印最深的人。弗洛伊德觉得艺术品一定要有真实的东西在里面。他欣赏蒙德里安的几何油画,虽然那些“格子画”跟他的风格差着十万八千里,他却说:“那些画就像所有的好作品一样,有现实世界的意境。我只对以某种方式体现的真实世界的艺术品感兴趣,我不会去关心它的风格是抽象的,或是其他什么形式。” 艺术家表现真实的手段完全出自他的气质。郑春龙习惯选择方形造形母题展开自己的画面布局和造势游戏,不仅表证了他在油画这个画种上有对于传统的继承和精进,同时更有一种将自己的艺术化入时代的自觉。“苗女系列”中的《苗女》组画、《山花》、《节日》、《晨光》等篇什,无论是背景还是物象本身,基本是由几何图形构成的。那些女孩子的银质头饰、衣饰挂片,其实是一些填充着微妙色块的几何图形。背景色调的调试和地面阴影的铺设,大刀阔斧的笔触,竟有中国传统山水“斧劈皴”的意味,这些,联起手来为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碑式”倾向。人体的曲线和块面均纳入几何图式,皆被率性地描绘。以鲜灰和冷暖为主的色彩对比形式的运用,显得温润跳脱,厚重生动。色彩明度的微妙变化,巧妙地透视出画面的纵深。《女人体》组画,选择对模特背影的描绘,这本身就有深刻的意味,让我们的脑海里翻腾起古希腊的人体雕塑,似乎还看到文艺复兴早期马萨乔的影子。我不能说他的这些“女人体”是完美的,可完美不等于难忘。如果一幅画里所有的部分都完美地连接起来,那这幅画绝对不可能是令人难忘的作品。如果油画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强烈的,就会让人联想到很多事情。这个主题的画作虽与“苗女系列”频繁调整变换的色块不同,人物双腿隐显的色块,臀部亮而白的皮肤色块,整个背部浅浅的亮灰调子,作品所呈现的色彩结构,以及画面上出现的“笔缺意到”和“未完成感”的故意,传达出了强烈的当代性。那是一种简约、理性、静穆之美。郑春龙游走在当代与古典之间,塑造了这种美之永恒。 关于表现真实,早先的观念只允许艺术家表现从自然中观察到的东西,所有由想象或回忆产生的东西,对构成一件造型艺术品来说都是虚假的,一钱不值。郑春龙的艺术当然表明了不是对这种看法的屈从,那么,寻找和追求一种当代性的表达,自然成为他整个行进路线中各个不同阶段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他探寻着超越踏实模仿的表现手段,并相信一条真理:如果一个画家无法使自己摆脱掉上一代的影响,必定会被淹没。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所崇拜的先驱者作品的直接影响,他必将在与自己志趣相投、形形色色的文明成果中寻求新的灵感之源。而如果画家是敏感的,他不会失去上一代人的贡献,因为不管他愿意与否,那些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浸入了他的生命本体。然而,让自己摆脱这种联系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他才能依照自己的天性,创造出某种新的生动而又有灵感的东西。塞尚就是从普桑身上获得灵感的。而塞尚也说过,“向有影响的大师挑战。” 《秋葵》系列显然饱含着郑春龙巨大的企图心。 优秀的画家不能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感受与他表现这种感受的方法区分开来。郑春龙的图画的全部安排都是富于表现力的,由物象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四周的空白、空间、比例,每样东西都起着一定作用。构图就是画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把各种不同的因素用装饰的方法按画家的意图安排的艺术。在“秋葵系列”的每一个画幅之中,每一部分都被看到,而且每一部分都起着赋予它的作用,不管它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艺术作品应该整体和谐。画面上凡是无用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多余的细节对主要因素来说,只会起到喧宾夺主的作用。 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苏轼认为,“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又有怀素自论草书云:“东却西,南却北,倒还起,断还续。”其所谓触遇成形者,并非乱涂乱划,这里面有辩证的道理:有来有去,相反相成,而驱笔之际,有“我”的一贯的“气”在,故变而不乱,是作书一法,这又何尝不是作画一法!画家“浩然之气”在胸,修养广阔而接引天地,运起笔来便自然无碍,写出景来,也就意趣盎然了。《秋葵》系列,浩气逼人。品读这些画,我们会忽略技法,强烈地感受到他创作中的真诚。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诚是绝对必要的,对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种真诚能给他所需要的巨大的勇气。如果没有这种意义重大的真诚,艺术家只能从一种影响飘向另一种影响,忘记去寻找他应该从创作中获得个人特点的基础。 依我看,我瞪大了眼睛看,怎么看《秋葵》系列的创作——正是这个“系列”,是郑春龙艺术语言发生嬗变的肇端。这种嬗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通晓绘画“现代性”在中国的意义,并不是哪个画家都敢于触碰的话题,有意无意的,这哥们儿去碰了。就是从《秋葵》开始,他比一般人更 抽象艺术的产生,标志着现代艺术无论从形态还是精神层面,已完全脱离一切具象形态而独立存在,标志着点、线、面、色彩终于有了属于自身的独立品格特征。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杰克逊·波洛克认为,现代艺术的着眼点是时间和空间,艺术是表现内在世界——活力、运动、情感及内在力量,而非图解社会。“缺乏描述,以表现或构成的方法表达概念”,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的基本特点。而撤销理性,则意味着从更为多元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绘画抽象性意趣的表达和探索,无疑就是艺术现代性的基本图谱。其实,就绘画作品本身而言,其基本元素从来都是抽象的,形、色彩、色调,点、线、面,以及绘画技法,等等。从根本上说,艺术从来不是给予答案而是给予思考。在这个语境里,抽象艺术完成了对绘画基本元素的激活和解放。马蒂斯甚至认为,德拉克罗瓦只画手的符号。他的观念是,一位美术家的重要性是由他引入美术语言中符号数量的多寡决定的。当画家对自然抱有真正的感情时,他就能够创造出对艺术家和观赏者都具有同等效用的符号。 绘画是以自我为媒介的一种表现。绘画并不一定非得画什么,纯粹色彩和形状的组合也能传递感情,因为内容是有时效性的,但形式永不过时。我的观念里,郑春龙的“山系列”,是纯粹的形式美学样本,带有抽象性的意蕴和表现主义的经略。《圣地》、《雪域》、《寒带》、《静地》、《山》、《辉煌》等,武断地截取了山岩的片断与动势,继而对其近乎人物肖像般地刻划,赋予作品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郁的人文情怀注入;画面几近简约精纯为无色彩,那些经由续接《苗女》而延展发扬的几何形状,此时已然纯化为一种标志性符号。粗砺率意的笔触,方斫凝重的色块,中国传统水墨山水“虚室生白”和“浮流”的情境营造,催生出灵性空间,将作品引渡至一个悠远宁静的诗意王国,完美地传达出“荒荒油云,浩浩长风”雄浑境界。 大概每个艺术家都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艺术中,当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明了的事不再理解,同时你身上仍然保持着精力,并且这种精力由于反对、压缩、凝聚的均衡作用更加强大之际,真理和现实就开始出现了。那时,你必须以最大的谦逊,用彻底的公正、纯洁和坦率的态度去表现它,如同一个圣徒走向祭坛领取圣餐一样,你的头脑仿佛处于真空状态。你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置于脑后,并且懂得如何保持自己的直觉生动而新鲜。 此时,于此处,我仿佛真的看到一个傻呆呆的郑春龙,眼前无限春光,身侧万千纷扰,都不再跟他有半毛钱关系,他就那么站着,站在烟波浩荡阔大无边的时空里,倔头倔脑而又万分小心地养护着他的“生动而新鲜”。 此时,于此处,我又在想两个十分不靠谱的问题:郑春龙是不是也听到了三千年前那个夜晚渭河边上的两声鸟叫?而《诗经》里,那年花开月正圆,那个“生动而新鲜”的年轻男子,会不会一直辗转到天亮? 艺术源于一种深刻的怀疑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 上帝为什么不容许人类修建巴别塔?其实,大洪水过后,上帝就指着天上的彩虹和人类立下约定: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过日子吧,我不会再用洪水淹死你们! 人类生性多疑。人类是个天生喜欢追问“为什么”的生物种群。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不时能够问出一句“为什么”,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主要依据。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镌刻着这样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面对两个女儿的巨大变化,竟然对自己的身份和理性产生了怀疑,不停地追问“我是谁”。《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武功臻于化境,因为不认识自己而走火入魔,“我是谁”这个问题就如同影子一样纠缠着他。那么,人类究竟为什么要修建巴别塔?人类修建巴别塔,该不是就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双脚站在那塔尖上问出一声“我是谁”吧? 圣经中记载,人类为了展示力量,聚于示拿,开始修一座通天塔,以此犯倔,和上帝扳扳手腕:凭什么俺要规规矩矩听从你来安排咱的生活?这是人类的自欺,是在玩自欺欺人,结果,连伟大的上帝也中招了。依我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类可能自己也没搞明白,他们骨子里早对上帝的安排充满了疑虑,他们怀疑上帝“小看”了自己,因此要证明一下,是证明给自己看,一边证明还一边怀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高更的这幅被收藏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油画,洞穿了人类的全部奥秘。 艺术源于一种深刻的怀疑。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柏拉图在模仿问题上对画家进行了指责,他认为绘画仅仅对真实物体的模仿是不够的。两位哲人的观点近乎趋同:模仿自然不应该是简单的再现。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艺术的产生,是出自人类对自然和自身不确定性的认识,从而进行再认识再创造的一个精神幻化过程,是认识自己的心灵求索,是物质世界内化为精神世界的心理转换游戏。与旁人不同,艺术家在做这个游戏时往往过于认真,甚至可以拿命去赌那噌噌飞转的命运轮盘。他们坚信,一切名副其实的艺术都是宗教的,不论它是一种线的创造还是一种色彩的创造,如果它不是宗教的,它就不存在了。如果它不是宗教的,它就仅仅是一种文献艺术,一种轶闻艺术,若是那样,艺术也就不存在了。文献艺术和轶闻艺术与艺术毫不相干,它们出现在文明的个别阶段,是用来向毫无艺术修养的人们解释和证明某些事情的。是一种宣教和灌输,它们注定是过时的艺术,或者干脆说,它们根本就“不是艺术”。 一幅画不会引起一种并不存在的情感。一幅优秀艺术家创作的绘画永远会激起一种摆脱现实的冲动,让我们腾起一种精神升华的感觉,同时沐浴在一种净化思想照亮情感的高尚的精神氛围里。 郑春龙的艺术创作,大抵是以一种怀斯式的乡土情怀再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没有像安德鲁·怀斯那样,毕其一生枯守着自己比一张邮票大不了几寸的家园,但是在艺术广阔的精神空间里,他的探索是从乡土之爱出发的,在经典主义玄远而可靠的方向上作出了诚挚的努力,没有附庸风雅,也没有自鸣清高。对于“秋葵系列”,他本人以为是做着某种精神转换的游戏,我却认为是他执着于乡土之爱的放达而自然的情感潮涌。同时也是艺术理想的移境换位:当画家来自生活的审美情结深化的时候,他的画面反而虚化了。艺术是往往其情愈深,其象愈虚。这批“秋葵画”,人物完全撤出,但活生生的人物就站在那里——或倒卧那里——自然的东西神化了,也就诗化了。有十多年,他一直倾心苗侗风情,多次深入黔东南采风,那些跃动在画家笔下的“苗女”,她们那缀满全身的银饰的叮当作响,那分分秒秒都在喷吐绽放的山野美人的韵味,牵着田野上的油菜花香,引着山间的竹风竹韵,朝我们走动弥漫过来,竟与那些“山石”和于瑟瑟秋风中兀自挺立的“秋葵”唱和一道,这分明是高天厚土散布涌流的芳香和辽阔,岂不也是画家那缱绻漫漶的乡愁? 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母乳,绘画则是画家对沉思和宁静的召唤,它抚慰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和休息。他们的感情,他们对现实美的观察和思考所强化的想像力,通过这些去增大色彩和图形的力量,因而,我们只需要那些有才能将其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转化为色彩和图形的画家。这样,人们才会看到世界的另一面,以及满足对这个世界和他们对自己的种种想像,在疑惑和平复疑惑的循环中,趋近和完成走向“认识我们自己”的可能。 年9月24日 北京丰台万绿园寓所 年9月30日 黑龙江省望奎县鼎鑫宾馆 王伏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职业作家、画家。 黑龙江省青冈县人。 当过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指导员,在团师旅军政治机关当过干事,先后在沈阳军区电视艺术中心和武警部队文工团任编剧。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高雪部队》、《高地纪略》,长篇小说《从这里到永远》、《越境》,电视连续剧《士官》、《陆军·陆军》,话剧《大江流》及油画等美术作品。 小说集《高雪部队》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小说《像飞一样》被编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 文学作品多次获奖。 年10月,国画《会师》入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军美术书法作品展览”。 部分绘画作品在报刊发表并被收藏。 邮箱:wfy .安卓开发总监复方斑蝥胶囊说明书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qinggangzx.com/qgxdl/876.html |
当前位置: 青冈县 >我读郑春龙的油画丨巴别塔和烂尾楼文王伏焱
时间:2017/11/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县委书记杨勇同志慰问贫困党员
- 下一篇文章: 平远荣获2017最美中国生态自然旅游休闲